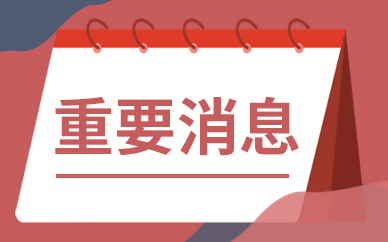原标题:海南周刊 | 纪念卡夫卡:镌刻于心的“中国情结”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140年前的布拉格,一个名叫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的男孩降生了,之后,他在短短41年的生命旅程里,把“荒诞”一词带进了世界文学史。
这几天,国内文学界铺天盖地都是卡夫卡的影子,人们用各种细致的方式,在各种媒介里,进行了一次各领域创作者所创造的“卡夫卡风”作品的综览。生前在保险公司任职,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卡夫卡,作品数量并不十分庞大,但他用《变形记》《乡村医生》《审判》《城堡》等作品作为原点,让后世的文学界长出了一棵体量无比庞大、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巨树。
呐喊是一生的精神基调
翻译家、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在述及卡夫卡的出场时,曾经说过,1883年7月3日,是个属于“世纪末”阴云笼罩的年代,“前途未卜”的灰暗情绪困扰着人们,令人不安、憋闷。这股情绪郁结的结果,是三十年后,一些有识之士在表现主义运动中找到突破口,大声地呐喊出来。卡夫卡生逢其时,于是,这种呐喊的情绪,确定了卡夫卡一生的精神基调。
卡夫卡属于犹太血统。那个年代,这个民族没有固定的家园,这让心思细腻的卡夫卡从小就蒙上了阴影。他的内心深处,隐匿着无家可归的漂泊感。而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作为成功的商人,历来只关心他的生意,同时,他对儿子的教育是一种强权家长制的管教方法,这使卡夫卡自小头顶就笼罩着强权的压力,他曾经发过这样的议论: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笼罩着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
卡夫卡大学时学的是法律,但他的兴趣是文学。他喜欢读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等人的作品,并开始习作。他最早的一本集子《观察》约于1902年写成。此时的卡夫卡并没有十分凸显自己的才华,但他的同窗中,有一双眼睛已经开始在他身上聚焦——这就是卡夫卡后来的知己马克斯·勃罗德。
卡夫卡于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实习一年后,于1908年开始在官办的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供职。他对于这份工作并没有多少兴趣,多次想摆脱以利于创作,但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22年因病势恶化被迫退休为止。但在他离开公司之前,他一直是“恪尽职守”的,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他的人缘一直很好。
从文学外走来的“悖谬”
在关于卡夫卡的各种赞誉中,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的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在我从事德语文学史研究期间,发现有两个人是从文学外走来的,一位是19世纪的毕希纳,一位是本世纪初的卡夫卡。”“从文学外走来”,意即这两人的作品并不符合固有的文学概念与规范,属于行外,然而,这“野”的最终却成了正宗的了。马耶尔认为,卡夫卡“改变了德意志语言”。这改变并非语言使用规则的改变,而是一种话语方式的改变,或可理解为语言固有观念的改变。卡夫卡一度被认为“野”的文学作品被公认为真正的文学,而卡夫卡本人,成了左右20世纪文学主潮的“现代文学”奠基者之一。
在1921年5月,37岁的卡夫卡和国内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音乐家和作家古斯塔夫·雅诺施谈话时,说了一个著名的自喻,这个自喻后来成为他的专属标签:
我是一只很不像样的鸟,我是一只寒鸦——一只卡夫卡鸟……对我来说不存在高空和远方。我迷惘困惑地在人们中间跳来跳去……实际上,我缺乏对闪光的东西的意识和感受力,因此,我连闪光的黑羽毛都没有。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
在这段话里,反复出现的“寒鸦”正是卡夫卡的名字“卡夫卡”(Kafka)在捷克语中的含义。有人说,这个名字就像某种冥冥之中的宿命一般,萦绕在卡夫卡41年的短暂人生中,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意象——一只寒鸦便足以摧毁整个天空。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业余作家在死后迸发出的巨大能量,直接引爆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并震惊了全世界。百年以来,这只孤独的寒鸦就像幽灵一般始终盘旋在黄昏的天际。
卡夫卡的这个自喻如此形象。而他的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说,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哲学术语“悖谬”有关。“悖谬”,一般是指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于卡夫卡而言,它既是哲学概念,亦是艺术方法,我们在谈论他的作品时,总是与荒诞相联系。这确乎是一种标签式的存在,因为许多认识卡夫卡的人都说,卡夫卡对一切日常的事情也表现出惊讶的神情,甚至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那么尴尬。奇特的是,当卡夫卡把这种思维特点作为艺术手法进行运用时,却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审美情趣。譬如《饥饿艺术家》中那位主人公以饥饿作为表演手段并作为艺术追求,他饿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的艺术越高……这就构成了悖谬。事实上,这种悖谬也贯彻于卡夫卡的生活中:他渴望婚姻和家庭,却屡次订婚又解约;他视写作如生命,临了却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一生活在父亲暴力的阴影下,却给父亲写过一封三万余字的长信而未寄出……他不停地建构,又在不停地解构他与父亲的关系,于卡夫卡而言,这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这种纠结,他后来在长篇小说《审判》里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
对中国文化极度痴迷
细察卡夫卡短暂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身上一直萦绕着深深的身份焦虑: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奥匈帝国,但他显然不是奥地利人;他虽然用德语写作,但他不是德国作家;他虽然出身犹太民族,但他与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却有着深刻的隔膜;他被奉为现代主义文学开山鼻祖,但在他的作品中已经透露出许多后现代主义的气息……这一切和卡夫卡独特的无所归依的身份紧密相联,也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叶廷芳先生所说的“悖谬”。
奇特的是,这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却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一种神思隽永、刻骨铭心的想象,他曾对未婚妻菲莉丝说:“中国学者总是在午夜两点钟的光景光临他的梦境”,甚至在给后者的信中直言“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奇特的大脑里出现了更多关于中国的天马行空而又意味深长的想象,他的神经甚至为中国的古典诗歌而疼痛。卡夫卡对中国的这种情结,我们在很多关于他的作品中都能读到,无论是他的挚友勃罗德所写的传记,还是他的忘年交古斯塔夫·雅诺施的《卡夫卡谈话录》,以及包括情书在内的诸多作品,如《一道圣旨》《中国长城建造时》《拒绝》《变形记》《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等等,我们都可以读出卡夫卡镌刻于心的“中国情结”。
在卡夫卡挚友勃罗德所讲述的卡夫卡“中国往事”和卡夫卡致菲莉丝的书信中,我们能读到卡夫卡对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古典诗歌的迷恋:汉斯·海尔曼《中国抒情诗:12世纪至今》、马丁·布伯《庄子语录和寓言》(1910年)、马丁·布伯《中国鬼怪与情爱故事》(1911年)、卫礼贤《中国民间故事集》(1914年)、汉斯·贝特格《中国之笛》(1918年)、克拉朋《李白诗集》……在给菲莉丝的书信里,卡夫卡反复演绎清代文人袁枚的《寒夜》诗:“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尽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他以中国古诗为媒,向女友表达了自己对婚姻的渴望,虽然最终未果。
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卡夫卡对杜甫和李白的魂牵梦绕,勃罗德清楚地记得,卡夫卡曾“以无与伦比的亲昵之情,背诵了杜甫致李白的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杜甫著名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头两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而在《卡夫卡谈话录》中,我们又读到卡夫卡对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倾心与熟稔。他甚至为雅诺施展示了《论语》《中庸》《道德经》《列子》《南华经》等的德文译本,并表示自己深入研究道家学说已经很久了。(杨道)
标签:
上一篇: 雨热无缝衔接!河南今天仍有40℃高温,明天一轮大范围降雨上线
下一篇: 最后一页